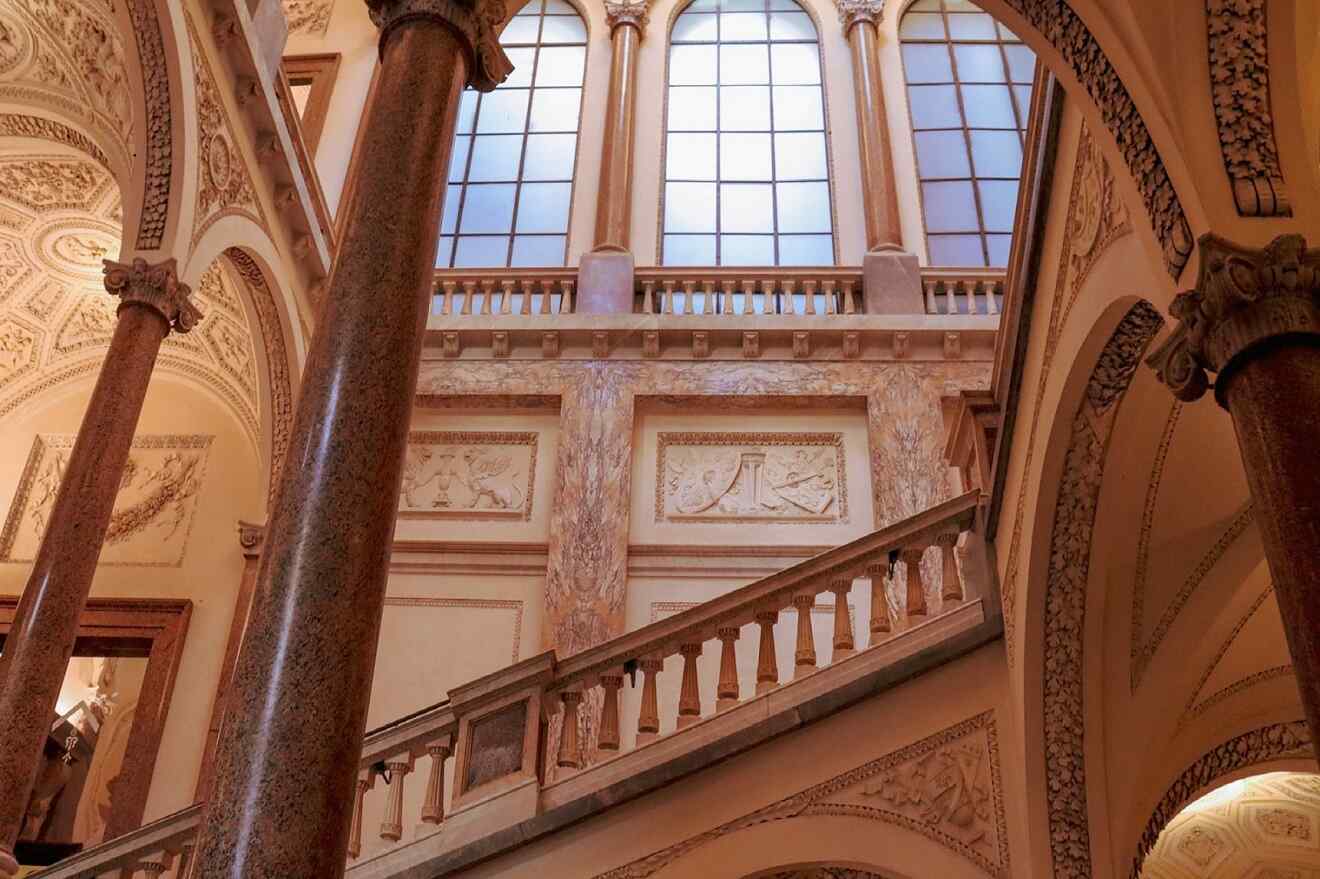圣诞节之约:纪念莫扎特诞辰260周年之尾声
---莫扎特与他的钢琴奏鸣曲
地点: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
时间:2016年12月25日14:30分
主讲:傅红 (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硕士导师)
王烈 (钢琴艺术指导、青年音乐学者)
活动简介:纪念莫扎特260年系列讲座终场收尾,此前5月、9月分别于听众分享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歌剧的赏析,此次将与大家分享他的钢琴奏鸣曲与变奏曲的创作。考虑到圣诞节的节日气氛,傅红教授也将演奏一些莫扎特之外的作品,例如拉威尔和巴托克。
摘: “莫扎特音乐不同于巴赫,它不是福音;也有别于贝多芬,它不是生活理解。他的音乐并不宣讲学说,更不表现自我。人们沿着这两个方向从他的作品、尤其晚期作品中所作的种种发掘,在我看来,似乎带有极大的人为性,因而极少启发性。莫扎特并不想说什么,他只是歌唱,只是传出声音。因此,他并不强加给听众什么,也不要求他们作出决断或者表明态度,而是让他们感到自由。”
文/ 卡尔·巴特
选自
《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1756年萨尔斯堡教堂神甫的施洗记录簿上写道:“尊敬的宫廷乐师莱奥波德·莫扎特先生及夫人玛丽亚·安娜·彼特林之婚生子约翰尼斯·克利斯托穆斯·沃尔夫冈古斯·特奥菲卢斯于1756年元月27日夜8时降生,。当年这个受洗男童的四个庄重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假如与第三个联系起来,便会使人立刻想到早他7年在法兰克福出生的另一个约翰·沃尔夫冈;假如与第二个名字加在一起,又会使人联想到那位约翰尼斯教父,为了表达对这位教父可爱的学说的敬意,便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克里斯托穆斯(“黄金之口”)。四个名字中常用并普遍为人所称道者是最后两个,而第四个名字特奥菲卢斯(上帝之爱)的拉丁文写法是阿马德乌斯(Amadeus),名字的主人一般将它改成“阿马德”(Amade)。
不过,人们万万不可以认为,认知我们讨论的人和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莫扎特丰富多彩的作品与短促而动荡的一生蕴含着一个解不开的算式,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秘密。必须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莫扎特的音乐(以及他的音乐所体现的他的人格)至今仍然如此激动人心。
如果谁对莫扎特仅一知半解就试图去讨论他,谁就很容易停留在仅仅用一些溢美之词去赞美他的阶段。基尔克果就是一例。他曾以威胁的口吻扬言,他将游说“从教堂司事到红衣主教的全体神职人员”,敦促他们承认莫扎特胜过所有伟大人物,否则,他将“退出他们的信仰”,与之决裂并建立一个“不仅尊莫扎特为至高至上者,而且只敬奉莫扎特一人”的教派。稳健持重的歌德不也是称莫扎特是音乐中高不可攀的“奇迹”吗?其他无数知名度稍逊的人更是如此,他们在将莫扎特与其前后的大师们作坦诚比较中进行评论时,心中想到的、嘴里说出的不也尽是“绝无仅有的”、“无可比拟的”、“至善至美的”这类词藻吗?当然,这些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只是也许有人会问:其本意究竞何在?这就是说,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们口头上在称颂莫扎特,而意之所瞩却是贝多芬或舒伯特,因为他们的最高成就莫扎特在其“晚期”创作中早就已经达到了。或者说,在莫扎特“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中就已经表现出了他从音乐上群星灿烂的18世纪所采纳的诸多风格形式中的一种。近代以来,人们作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对他的全部作品(完全像对待《新约》和《旧约》那样!)就他创作的早期和晚期所接收和吸收的来自多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如来自约·塞·巴赫的儿子们以及约·塞·巴赫本人的影响,来自韩德尔、格鲁克、、意大利及法国的作曲家们的影响。他之“独一无二”是否恰恰在于他不可能、也不想成为革新者、革命者,不可能、也不愿意有任何特别之处,他只能、也希望在他那个时代的音乐长河之中并依靠这条长河而生活和创作?是否恰恰在于他只能、也希望将音乐当作他独有的本己之物而使之发出声响?他之“独一无二”是否恰恰在于他只能、也希望作为学生——正是因此而“无可比拟”地成为大师?这里重要的也许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音乐吧?莫扎持早期和晚期作品的那种不容与他人混淆的原初本音是否与音乐之原初本音完全相同?难道他以其超越时间的形式击中和拨动了音乐的此一原初本音?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很难甚至不可能精确地为莫扎特的音乐下定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在对自己或别人解释莫扎特其人时,便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无济于事的夸张词藻吗?
有人曾经说,他是一个孩子(甚至是“神性的”孩子),是一个用他的音乐对我们谈话的“永恒的少年”。他令人痛心的短暂生命可能是他获得此一称号的缘由;但还有另一些缘由,这便是他对一切实际事务(根据他姐姐对他的尖刻评语,尤其就他处理婚姻以及一切与钱有关的事情上)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无知,他在与人交谈时,尤其在信件中总爱发一些幼稚可笑的噱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仍然如此。最令人惊奇的是,据可靠材料证明,他事实上最爱在严肃工作的时候调笑发噱。倘若人们将他看成是“孩子”(布克哈特曾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是人们在对他进行思考;倘若他们想到这个真正掌握着艺术技巧并不断以新的创作使之日臻完美的人懂得,不可用他的艺术——真正从未如此!——给他的听众以重负,而是每次都重新让他们参与他自由的、可以说童稚的游戏,那么,他们对他的理解便深入了一步。倘若他们注意到他——如他们所说的——“真正像一个纯洁的孩子那样”能够“一口气地对着我们痛哭,对着我们大笑,而又不容我们询问其原因”,那么对他的理解便又深入了一步。现在,我想提请人们考虑的是,命运恰恰不容许莫扎特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孩子”。
他3岁时就开始弹钢琴,4岁时已经准确无误地弹奏短小乐曲,5岁能谱写小品;与此同时,他在父亲指导下不倦地学习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算术及许多音乐知识。他6岁时进行第一次旅行演出,7岁时开始第二次,即那次为时3年半的巡回演出(他到过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在返程中途经日内瓦、洛桑、伯尔尼、苏黎士、温特图尔、沙夫豪森!)。从14岁到17岁—这期问已经在持续不断地谱写歌剧、交响曲、弥撒曲、四重奏等——他曾三次去意大利巡回演出,而且从此便再也没有间断过羁旅生活。难道这是一个孩子?不,这是一个戴礼帽、佩短剑(歌德于1763年在法兰克福见到他时就是这副装束)、风度翩翩、永不休止地演出和创作的真正神童:他为伟大的玛丽亚·特蕾西亚、法国国王(不要忘记还有蓬巴杜夫人!)和英国国王所赏识和嘉奖,他接受专家们的考试,他被教皇克莱门斯14世授予“骑士”称号,并被波伦尼亚的一个音乐学术团体吸收为会员!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严谨而练达的父亲的指导(在他心目中,父亲“仅次于上帝”)。在父亲看来,为了而发展儿子的“天才”和传扬儿子的“声名”(而且是在孩子本人完全同意和参与之下进行的)是正确和必要的。对于瑞士人,听起来最可怕的是:“沃尔菲尔”被完全剥夺或者说免除了入学读书此一善举!不然他会不堪其苦的!莫扎特不足36岁便因此而死于莫名疾患的病根大概应从他这种反常的青少年时代去寻找。不过,他当时没有变成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野孩子也算是一大奇迹了,其原因大概也是由于他没有时间去撒野吧。他从来不曾作过寻常意义上的孩子:正是付出此一代价,他方才成为另一种更高一层意义上的“孩子”。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否则便会作荒唐之想,发荒唐之言。
有一段时间,人们在说明莫扎特音乐时偏爱用“优美”或“欢快”这类词,并将他本人描绘为永远欢悦人心灵的洛可可的宣讲者,甚至称他为太阳神。一位瑞士人,与他同样早逝的名叫弗勒利希(F.Th.Frohlich,1803—1836)的阿劳的音乐总监称颂他是“一个欢乐童子”,“喜气洋洋的双颊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在“永远湛蓝的天空下”游荡着。但这不是莫扎特,既非他的生活,更非他的音乐。关于莫扎特是否“幸福”的问题,一个与莫扎特同时代并认识他本人的英国人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从来不曾幸福过。”当人们谈到他的音乐所具有的令人感到幸福的品格时,应该想到这一点!还有关于他的爱情的猜测(这远非是猜测):他虽然经常堕入情网,但他却从未真正爱过——除了音乐夫人——哪一个女性。另外,他与父亲日渐冷淡的关系,在萨尔茨堡大主教科洛拉多处供职时令人窒息的环境,此后在维也纳多次求职所遭受的挫折,家庭长期的经济窘迫,再加上病魔缠身等等,这一切都给他造成痛苦。莫扎特很爱笑,然而实际上这并非由于他有许多值得笑的事,而是因为他——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没有值得发笑的事仍然可以并能够笑。真实的情况是——这也许是莫扎特这个“欢乐童子”的童话的真实性之所在——他(如本世纪一位聪明的法国人所说)从不知怀疑为何物。
这便是他的音乐所固有的激动人而又安抚人的性质。它显然是来自这样一个高层面,从此一高层面上(人们在那里将认知一切!)同时观察到了此在的右侧与左侧,即欢乐与悲痛、善与恶、生与死的现实及其局限。啊,我们善良的内格里(Hans Georg Nagli,谱写《最神圣之夜》的作曲家!),他竟因莫扎特作品所具有的如此鲜明的反差而在事后对他大张挞伐!人们怎么会因此而对他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解呢?莫扎特不是开朗活泼的人,不是乐观主义者(他的明快悦耳的大调乐章、他的小夜曲和嬉游曲,甚至他的《费加罗》和《一切人全都如此》都无法证明他是这种人!)。但他也并非忧郁型的人,并非悲观主义者(他的大型和小型的8小调交响曲、d小调钢琴协奏曲、不协和音弦乐四重奏,以至他的《唐·乔万尼》的序曲和尾声都无法证明他是这种人!),他的音乐表现的是现实生活的冲突,然而,尽管如此,其背景却是上帝的善良造物,因此(这大概便是关于他战无不胜的“优美”的议论所指的东西吧)而永远处于从左侧向右侧的转化之中,即处在从悲向欢、从恶向善、从死向生的转化之中而从不会逆向转化。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单调乏味的平野,也没有深奥莫测的绝地。他既不容许自己便宜行事,也不放任自己失去节律。他只是在一定的局限之内表现一切事物的真相。这就是他的音乐美妙、悦耳、动人之所在。我不知道另外还有谁的音乐值得人们作如此评说。
莫扎特音乐是包罗万有的,人们不禁为其中所表达的广泛内容而叹赏不已:苍天与大地、自然与人类、悲剧与喜剧、情感之各种形式的表露与深沉的内在宁静、圣母玛利亚与超凡的魔鬼、教堂大弥撒、的奇迹庆典与舞厅、笨伯与聪明人、懦夫与(真、假)英雄、忠诚者与奸佞小人、贵族与农夫、巴巴基诺与萨拉斯特洛。他似乎并不偏爱某些人、某些东西,而是爱一切人、一切东西:犹如普照一切的阳光,犹如浸润一切的雨蹬,这反映在——如果我没有听错话——他无限亲切、却又不似并非有意使然的风格之中。他总是以这种风格塑造和协调人的歌声或(在协奏曲中)主导的独奏乐器与伴奏的(不,通常绝不仅仅是伴奏的)弦乐器和管乐器之间的关系。人们百听不厌的不正是莫扎特乐队中那发生着、躁动着和激动着的东西?不正是那种种出人意料而又正当其时出现并以其特殊的高低音和音色而达到完美境界的东西?这一切不正是整个宇宙以缩微形式被表现于音响之中?显然,作为人的莫扎特听见了宇宙之音并使它——他自身只起媒介作用——歌唱起来。人们的确可以把这称之为“无可比拟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有待破解的谜。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表明,莫扎特事实上对他那个时代丰富的自然和历史科学、甚至对(除音乐以外的)艺术,如古典文学,根本不感兴趣。他有歌德的诗集,但他与歌德的关系只具体表现在为他那首《紫罗兰之歌》谱曲。
他曾提到过诗人格勒特的逝世(在他童年时代写的一封信中将诗人写成格雷尔特),他还对——1777年在曼海姆与之匆忙认识的——诗人维兰德作过幽默的描绘。据我所知,这就是他留下的文献中关于当时的文学所记载的全部内容。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一个名叫康德(I.Kant)的同时代人的存在!在他的众多信件中,我不知道有哪封信曾谈到过他对故乡和他旅行过的国家的风光和建筑的深刻印象——可以说,全都是浮泛的描写。像默里克在他的著名中篇小说中关于莫扎特如何享受他的“布拉格之旅”的描写是诗人的创作而非生活的真实。因此,希望从对古老的萨尔茨堡及其周围环境的研究着手来理解莫扎特,这看来出于好心,但却是徒劳的。显然,,至少是不曾为之所动。在这里是否应提一下关于他的一段轶闻?据说,他6岁时在维也纳王宫光洁的地面险些跌跤,当时幸得一位同龄的玛丽·安托内特大公小姐,即后来不幸的法国王后的扶持。对这一扶持,莫扎特不假思索地立即提出结婚动议作为报答。事实上,他毕生所直接关注的——除了他变化不定的人事和职业关系——似乎只是与音乐有关的东西。问题是,从莫扎特的音乐看,他无所不知,至少像歌德那样博学,尽管他没有歌德那双全面观察自然、历史和艺术的眼睛;毫无疑问,他胜过历代千千万万比他读书更多的,即通常说的“更有学养的”、更有兴趣的通世事知人情者;那么,他从哪里得到这一切知识的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想必他所具有的某些感官使他事实上有能力冲破他那种古怪的表面上的封闭状态,摄取他显然善于表现的世间万象吧。
莫扎特音乐不同于巴赫,它不是福音;也有别于贝多芬,它不是生活理解。他的音乐并不宣讲学说,更不表现自我。人们沿着这两个方向从他的作品、尤其晚期作品中所作的种种发掘,在我看来,似乎带有极大的人为性,因而极少启发性。莫扎特并不想说什么,他只是歌唱,只是传出声音。因此,他并不强加给听众什么,也不要求他们作出决断或者表明态度,而是让他们感到自由。从他的音乐中所期待的欢乐是从人们接受这一事实开始的。他曾将人的死亡称作他日日思念的真正的好朋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果真是这么做的。然而,即便对这一点他也没有大事渲染,而只是让人去揣测。莫扎特也不想宣扬对上帝的赞美,而是实实在在地力行,这表现在他的谦恭态度之中: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件乐器,他只是让人去谛听他显然听见的东西,那是来自上帝造物浸润着他、在他心灵中升华,而现在又从他心灵中逸出的东西。
他的音乐不可能是他安魂弥撒的音乐;反之亦然:他不可能使唱c小调弥撒曲中的《赞美您》或者《基督降生》的女高音与唱《费加罗》中《你们这些知人内心欲求的人》的侍童唱出同一个曲调,虽然他明显地赋予前者和后者同一种音色。他倾听文字,他尊重文字在此一处或彼一处所具有的特定内涵和品格,然后为此一处或彼一处的文字谱出音乐,不过,这是他自己的音乐——一种受文字约束而又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立构成体。至于他的音乐以这样一种处理方法是否与宗教性文字相合,那么人们应该逐一进行个案分析(而不可先入为主地采用将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区别开来的一般方法)。这样,人们当会愈来率深刻地——当然往往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以这种处理方法谱写的音乐恰恰符合宗教文辞的客观内容。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宗教音乐也是从这样一个所在听知而又再现出来的,从此一所在虽然不可能将上帝与世界合为一体,然而宗教与世界(彼此既不可混淆,也不可交换)之间的纯然相对的差别、它们最终的同属性质却是可以认识并且已经认识到了的:两者都从上帝而来,两者都向上帝而去。
最后,还有一个令人一想到便不胜伤心的问题:如果考虑到莫扎特短短的创作时间,人们便会发现,他留给我们的作品数量是惊人的。但是,他没有为我们留下来,而且我们永远无从知道的作品的数量更加惊人;因为在他生命的各个时期他都偏爱即兴创作,这就是说,在钢琴上自由虚构随意演奏:在公开的音乐会上也罢,或者更常常是面对几个听众连续演奏数小时之久。而此时所创作的东西事后并没有记录下来——这是整整一个曾经发出一次美妙音响然而却永远消失了的莫扎特音乐世界。
莫扎特的相貌如何?当然不像大多数保存下来的他的画像上的样子(它们全都将他画得有点像所谓的太阳神!)。他的连襟约瑟夫·朗格1782年绘的那幅(末完成)油画也许从神态到相貌都接近他本人。他有一对蓝色的眸子,一个尖尖的稍长的鼻子,是(据另一位英国人的描述)“一个显然很矮小的人,身材瘦削,面色苍白,有一头他似乎为之感到自豪的浓密金发”。此外,他喜欢打弹子、跳舞、饮番趣酒,“我曾见过他一次喝很多这种饮料”。这肯定不是一位立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的身分和职业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当他坐在钢琴前面时,他方才为人所注意(也许只有这时他的声音方才有人倾听)。这时他方才成为伟大的莫扎特。让我们感谢他,他至少在后来一再被演奏的乐曲之强有力的余音中使我们能够接近他。
摘自网友分享的“卡尔·巴特、汉斯·昆著,朱雁冰、李承言译 ”《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