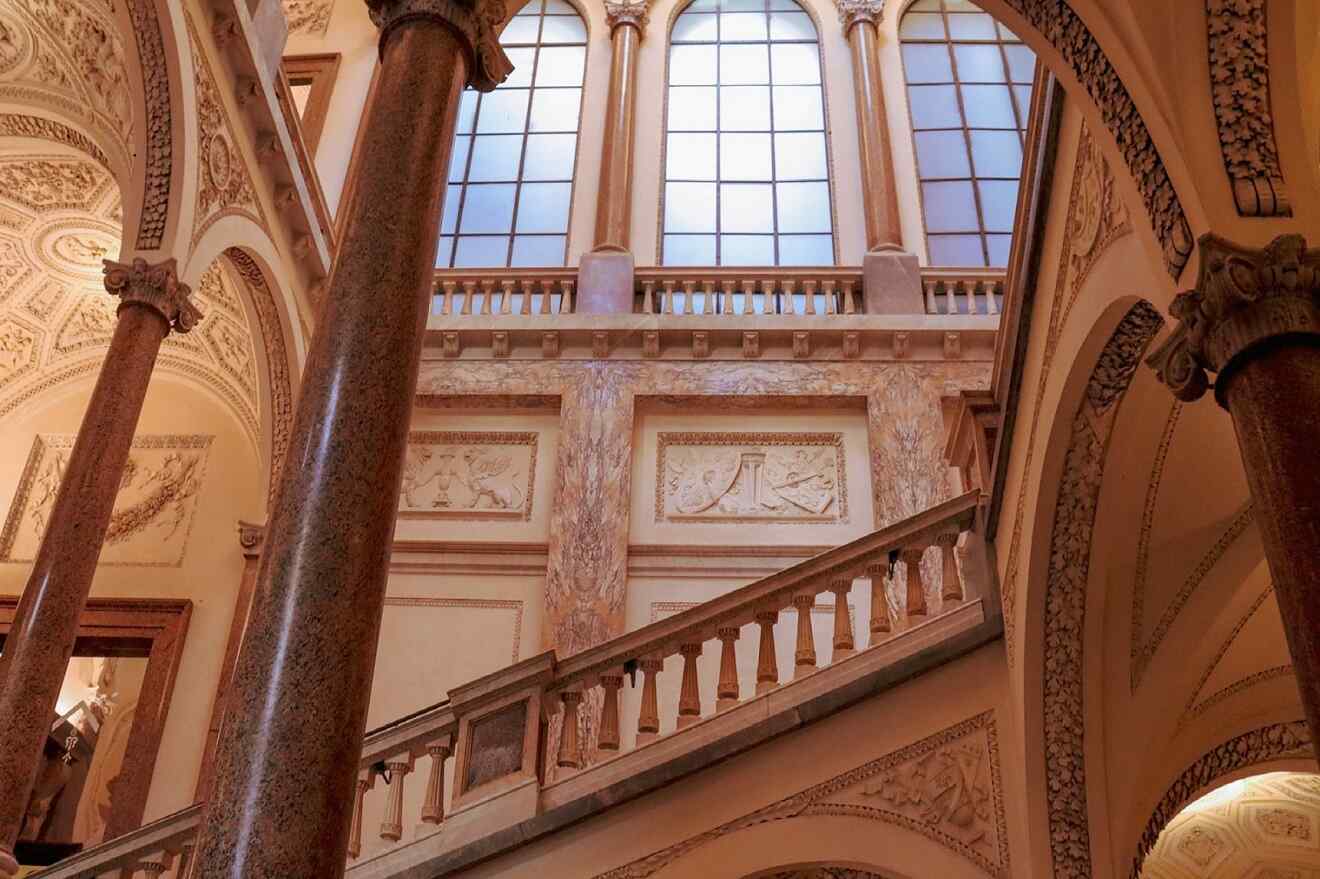在西方传统中,有两种思想领域塑造了对一种超越死亡的生活的期待:灵魂不死的希腊学说和死者复活的犹太——的希望。
—— 【德】潘能伯格
文 | 王少明
作为徒的莫扎特,尤其他的晚期作品,如歌剧《魔笛》、最后三首交响乐、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单簧管五重奏及协奏曲、《安魂曲》等这些被专家称为“神界”的音乐,无不浸润着文化的影响,反映出对“上帝之城”的眷恋,以及超越死亡和肯定生命的情愫。
歌剧《魔笛》海报
曾有人为他游说“从教堂司事到红衣主教的全体神职人员“敦促他们承认莫扎特胜过所有伟大人物,否则,他将“退出他们的信仰”,与之决裂并建立一个不仅尊莫扎特为至高至上者,而且只敬奉莫扎特一人的教派。这事实上是在把莫扎特奉若神明。
而《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一书的两位作者卡尔·巴特、汉斯·昆则采取了另一条道路。他们既未神化莫扎特,亦未认可他只是一位完全专注于世俗生活、轻浮的、童真的、甚至是幼稚的“阳光少年”。
少年莫扎特
在两位神学家眼中,莫扎特是作为一位有信仰的基督徒(在汉斯·昆眼中则特别是一位天主教徒)而进行创作的,并且具有“超验的踪迹”。
也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言:莫扎特的音乐不同于巴赫,它不是福音;也有别于贝多芬,它不是生活理解;或他只是歌唱,只是传出声音。事实上 莫扎特晚期的作品,尽管同巴赫、贝多芬在总体风格上有所不同,但从音乐的内涵看,他的音乐既是他宗教信仰的反映和启蒙运动产物,也是他个人悲剧生活的一种折射,既是他超越死亡的福音,也是他对个人生命中爱的一种肯定。
1787年4月,他在给父亲信中写道:“严格说来,死亡是人生的真正的终结目的,死亡是人类的忠实的、最好的朋友,这几年来我和这位朋友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他的形象不仅不再使我害怕,而且能使我感到安宁,获得安慰。感谢上帝使我认识到死亡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我虽年轻,可是我每天上床都会想到也许我活不到明天。认识我的人谁也不能说我流露出过抑郁、忧伤的心情。”
莫扎特与姐姐、父亲
后来还多次写信谈到预知死的来临以及对死的态度,不仅如此,莫扎特晚期的作品越来越多地渗透了他对死神和对上帝的严肃思考,不过其态度是相当乐观的。
但他又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有神学家汉斯·昆称之为“人性,太人性”的对人生无节制、非道德的贪恋行为如、通奸、撒谎、贪财、挥金如土等,这种贪恋性的人性弱点又铸就了他在世俗生活中“爱”与“死”的惨剧。
小莫扎特与爸爸、姐姐
据学界最近研究表明:他与弗朗茨(即情妇兰妮的丈夫)的死亡约定,又彰显出他为了爱愿意接受世俗的惩罚尤其是勇敢面对死亡的一份从容与淡定,因为他相信上帝会拯救并饶恕他。
正如《莫扎特的爱与死》的作者许靖华在评价莫扎特1791年创作《降B大调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所传达的境界:“以心中的爱、臣服、谦卑,去全盘接受自身的命运。他通过音乐服侍上帝,换来的报酬尽管是兰妮的爱……以及死亡”。
《第27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莫扎特梦寐以求的“德语严肃歌剧”《魔笛》,也是他最后一部严格意义的歌剧。歌剧中,他借助神话故事,不仅表达了他所在的宗教组织的理想如平等、博爱、宽容、自由等,更表达了对上帝、对女人、对儿童那种深厚的爱愿。
尽管这种爱愿交织着仇恨,如对夜后的丑化,但他最终把这种仇恨融入到爱流中,剧中的各种不同人物复杂多变的个性在他的神来之笔的音乐中达到极致的和谐。
《魔笛》中夜后的唱段“仇恨的火焰”
《安魂曲》与其说是受约于瓦斯格·史都帕伯爵所写,不如说是为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而创。曲中我们可以聆听到他直面爱与死那种从容而又铿锵地走向上帝的脚步声,这意味着他跟上帝越来越近,越来越成了上帝传达爱的的笛子。
《·旧约》有言:“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曲中反映了文化把死作为走向“上帝之城”进程中的一道凯旋门,为完成使命而死是“爱”的境界。“上帝的意愿,也就是我的意愿”———这是莫扎特在许多书信中一再表述的一句自白。
如果说他早期信仰的上帝带有某种外在强制性,那么,他人生最后十年尤其死前几年所信赖的上帝则是内在的。他承受的灾难不亚于贝多芬,如果说贝多芬在晚年通过音乐还找到了世俗的快乐,甚至死后的葬礼仪式隆重至数万人加入。
那么,莫扎特的晚年可谓度日如年:疾病的折磨、经济的负债、情感的纠结、死亡的约定等。死后葬礼不仅参者寥寥,草草葬于公墓,甚至后来连其墓地也难以寻辨。
莫扎特临终
在他晚期作品中,我更有感于他的两部钢琴协奏曲,即1786年创作的《A大调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和1791年创作的《降B大调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因为正好证明了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的评价:“它是一种‘保持性’ 力量音乐。”
在这两部钢琴作品中,我感受到的更是一种从宇宙深层结构浮现出来的光影,而这光影黑白两分,正好对应了黑白相间的钢琴键盘。黑白代表一种宇宙阴阳两级的张力结构,而这种张力结构意味着生和死、痛苦与快乐、天堂与地狱、肉体与灵魂、天使与魔鬼在作品中获得了一种莱布尼兹式的“预定和谐”。
作品似乎洞察了上帝诘难人生的所有秘密,透射出莫扎特对人类生存感受的感性学深度。然而正是这种感受,使宇宙的深层结构缩影般镶嵌在他的作品中,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之谜被莫扎特用音乐给破解了。
莫扎特《安魂曲》“圣哉经”选段
破解的密码是爱,或者说使生和死、痛苦与快乐、天堂与地狱、肉体与灵魂达到“预定和谐”的基础是爱。正是这种爱,死亡变得不仅不可怕,而且具有“回老家”般的归属感。正如莫扎特给他父亲信中所言:“活着也并不是一种地狱或炼狱般的煎熬,而是一种精神仪式。”
莫扎特创作的这种朝圣过程不是外在规定的强加,而是内在灵魂的自觉。这一过程尽管痛苦,然而正是这种痛苦才不断使心灵的快乐感具有超越性而变得高贵,人在这一痛苦中感受着生命的超验意义。
从这一前提出发,痛苦只不过是快乐的预演形式,地狱不过是天堂的客栈,肉体的受难不过是为了灵魂更好的得救。也只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在莫扎特作品中“超越死亡和肯定生命”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在贝多芬是自我否定式的,而在莫扎特超验和神启。如果说贝多芬悲剧的美学境界即爱的境界是通过多次毁灭性的打击而不断升华才达到的话,那么,莫扎特对悲剧超越而实现美学境界则要直接得多。
与其说他没有多少内心分裂的痛苦,不如说他把这种痛苦直接交给他心中的天主给无形地化解了。由于他的痛苦具有内在的神助性,所以他创作的灵感就好像被天主爱的舌唇轻吻过,其作品不带任何世俗的悲剧色彩和人生创痛感。
总之,莫扎特晚期作品把超越死亡和肯定生命这人生的两极竟然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让它相通相融,密合无间。这不单纯是创作的技巧,更是一种对生命的爱和智慧。
因为宇宙是个大的生命体,个体生命的存在只不过是从这个大的生命体中暂时脱离出来,而死亡意味着再以别一种生命形式回到宇宙生命之流中。既然是另一种生命形式,那么莫扎特在音乐中所显示出来的超越死亡与肯定生命就是一致的。
特约作者
王少明
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星海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非遗”专家,著有《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反思》《神唇之笛》《岭南乐空中的缪斯》。
爱音乐 爱艺术 爱审美
敬请关注沥姐说
编辑排版 | 沥姐
配图配乐 | 沥姐